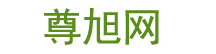母亲的忏悔
作为一个母亲,我深知自己是一个不合格的母亲。那天,我又打了女儿的脸。因为她学习时总偷懒,看着挺用功的,其实,用在偷偷的玩。
于是,我又一次压抑不住怒火。狠狠地打了女儿的脸。我在这里想说的是,我知道暴力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可是,我总是压抑不住冲动。
孩子到了青春期了,叛逆了。可是,作为妈妈的我并没有成长。有人说,青春期前的孩子有多听话,青春期时,他就有多叛逆。没有叛逆就没有成长。可是,作为妈妈,我连自己要成长的意识都没有。
问题的严重性日益突出,孩子越来越自卑。胆小。可我这是 在干什么呢?总是动手打他。总是希望他能停留在八周岁以前的状态,什么都听我的,挨了打也不哭不闹……
哦,原来我是世界上最失败的母亲。就要亲手葬送自己孩子的人生。孩子大了,还有自己的主意了,而且该有为自己的事情拿主意的权利了。
我错了,好几个不眠之夜,我深深的忏悔。女儿,原谅妈妈,我是该做一个合格的妈妈。我也该现在好好学习如何做一个好妈妈。
母亲的忏悔
父亲是在我刚刚记事的那一年去世的。那一年母亲二十六岁。我记得母亲哭得死去活来,父亲都埋进坟里了,母亲还挣扎着跑到父亲坟上号啕着愤怒地扒那坟,谁也劝不起她,大娘婶婶们就把我叫到一边悄声嘱咐了一番,我就一边给她擦眼泪,一边哭着说:咱回家!长大了我管你,我好好孝顺你娘,回家吧,回家!这是大娘婶婶们的主意,果然很灵,母亲渐渐停止了哭泣,看我一眼,又看我一眼,毅然站起来,拍打拍打衣襟,领上我回家了。就是在这一刻,我的母亲――一个二十六岁的年轻女人,决定和一个瘦弱的六岁孩子厮守终身了。母亲牵着我的手,那一长一短两个身影在乡亲们面前走过的时候,乡亲们流下了怜悯的泪水。就这样,母亲领着我这个不肖之子,在漫漫人生路上一走就是近半个世纪 那日子本来艰辛,父亲一去,剩下孤儿寡母,那日月就更艰难了。母亲是拼命做活的。白天下地,夜晚做针线,没见她片刻停闲过。白天还好,夜晚一拿起针线来,就嘤嘤地哭泣,渐渐,那嘤嘤哭声就变成了一支哀怨的曲儿,倾诉自己悲凉身世的一支曲儿。她早年父母双亡,如今又失去了丈夫,她的命运是够悲凉的。她没有一晚不做针线,也没有一晚上不哭泣。自己的针线做完了,就帮大娘婶婶们做,然后就做鞋卖。那鞋叫“浅鞋”,就是前脸上有一个翘勾勾的那种鞋子。如今已见不到了,那时我们家乡下苦力的男人,都穿那种鞋。做好三五双,就可以拿剑集上卖。母亲年轻时很漂亮,手功又好,那鞋往往一放下,就一抢而光了。也遇上个把图谋不轨的坏男人,但是母亲眼里只有鞋和钱,从不抬一下眼皮和多说半句话。父亲去世后,那鞋母亲大约做了三五年光景。母亲是在扯不完的针线哼不完的曲儿流不完的泪水中,苦熬着一个个寂寞的夜晚,企盼着我一天天长大 白天母亲却变成了另一个人。在人面前她一直挺胸昂首男人样操劳着地里的农活。雇人也罢,自己耕作也罢,从不表现出一点儿女人的软弱。男人又怎样?――她经常这样说。我家的地,有几年种得真比一些有男人的人家都好。对我也一样。我就不信一个寡妇教导不出好孩子来!――她也经常这样说。的确,父亲一去世,她就用她特有的方式管教我了。她自己不停地做活,也绝不允许我有一刻安闲。我数不清挎烂了多少个柴筐子和背烂了多少把粪篮子就是力所不能及的活,她也厉声撵我去干。刚刚扛动锄头的时候,就叫我去锄地了;担筲挑起来刚刚离开地皮的时候,就叫我去浇庄稼了稍一怠慢,会挨骂的。母亲的嗓门很好,她骂我的声音一条街的人都能听到。至今我都不明白,她为什么总是用那么高的嗓门骂我,让一街人都听到。 母亲干活又当男又当女,我也不例外。很小的时候,我就会烧火做饭了。已经九十七岁的我伯母,还经常说起我小时候烧火做饭的事情。伯母说你光着腚上下无根线,一顿火烧下来,浑身抹得像小鬼,小鸡鸡都是黑的谁见了谁笑。我当然记得,我还记得有一次母亲要去雇短工,她把我叫醒后,怕我再睡过去,就把我拉起来,用枕头、被子栽住我,一遍一遍嘱咐我烧一锅汤,等短工干活回来喝。母亲走了后,我还是一歪身子睡了过去。小孩子本来觉多,又日复一日没完没了地干活,我实在是太疲劳、太困了。直到母亲领着短工,在地里干了一大早晨活了,我还在睡梦中。母亲回来,一摸那锅是凉的,顿时雷霆大发!这回是一顿好打!如果不是三婶过来把她拉住,还不知道把我打成什么样子呢。母亲的妯娌中,数三婶最善良也最疼我,父亲临终时就跟母亲说过,你若嫁人,就把孩子交给他三婶,孩子就掉不了地下。想不到母亲妯娌四个,数她走得早。她是一九七八年去世的。三婶每次见母亲骂我或打我,总是把母亲数落一顿的,无非是说才几岁的孩子,人家这么大的孩子都到处跑着玩呢你把他逼出毛病来,看谁管你!这回三婶见她打我厉害,着实生气了,她红着眼圈指着母亲骂起来――你这个女人比后娘还歹毒!就是后娘,也没有这样待孩子的。如果孩子碍你什么,把孩子交给我,你走好了这是三婶气极的话,也是触动母亲心尖的话。三婶自如言语有失了,可是话己收不回了。母亲听了这话,马匕就愣住了,接着就冷笑一声说:好,我走!这话可是你说的,我这就走!说完,疯了似的跑了出去。等我和三婶回过神来,已不见她的人影了。 母亲的出走,惊动了四邻。虽然已经解放了,一个旺族的寡妇改嫁,仍被视为耻辱的。再说,我虽小,但毕竟代表着这个家族的一支血脉,乡亲们是很看重的。如果母亲有个闪失,是不好向耿家的祖宗交代的。结果,人们的担心是多余的,人们很快在父亲坟上找到,她。她在父亲坟前拼命哭诉她的艰难、哭诉她的委屈最后是长辈们出面,三婶在众人面前向母亲赔了不是,地里的活儿大家一齐出力帮着做了,母亲才平静卜.来。 这件事发生以后,母亲并没有改变对我的严厉管教(很难说不是暴虐)。相反,我在她面前,比以往更加谨小慎微了。在我的童年生活中,我没有无忧无虑地玩耍过的记忆。我没有欢乐的童年,没有!我也曾反抗过,比如拾柴时把楂子头撑在筐底下;锄地时光锄地头;给庄稼浇水只浇地皮(一筲水就浇一大片)为的是能跟小伙伴们玩一会儿。掏鸟蛋呀、捉蛐蛐呀、摸老鸹呀实在太诱人了。可是,这些怎能瞒得过母亲,那后果是可想而知的 晚上母亲的眼泪,白天不堪负重的农活,加上母亲的怪戾暴虐和不近人情有一段时间我真不想再忍受下去了。我感到我生活在苦难之中――心灵的苦难!特别是当我高小毕业再没有上学的机会以后,这种苦难感在成倍地增加着 在我的记忆里,母亲并不是一开始就这样的。她的坏脾气是同那年的饥荒相伴而来的。我说的饥荒不是众所周知的六零年,而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那次“统购统销”工作之后的那一年。记得母亲没完没了地开会,开会回来就称粮;再开会再称粮称‘次粮,母亲的脾气就坏一次;称一次粮,母亲的脾气就坏一次这时我如果让她稍不顺心,她就会歇斯底里地发作,发作过后平静下来,就说:我不跟你发脾气跟谁发?人家都是男人去开会,我却连个商量的人儿也没有。人家整我,逼我交粮,说咱人口少,得多交 咱攒下这点粮容易? 母亲吃亏就吃在她的犟脾气上。她竟然一气之卜.当着干部的面,把所有存粮全交上了。盛粮的家什都见底了,母亲不再开会了,我们的日子也就没法过下去了。这以后,母亲的脾气更大了,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 最让我不能忍受的是,她竟然嫌我吃得多!怎么又吃?你长了几个肚子?――母亲经常这样责怪我。吃什么呀?不过是揉碎了的树叶子捂成的窝窝头,或者是一锅菜糊糊!连这些也没得下锅的时候,母亲挎起篮子,拖上棍子,打算领卜我去讨饭!却几次拿起来,又放不下不了决心!最后还是咬咬牙,说:人家能过得去,咱也能过得去!最终没有外出去讨饭。 母亲忏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