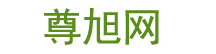《缅甸的竖琴》讲了什么?如何评价?
在二战接近尾声的时候,盟军在东南亚的反攻使日军全线崩溃,其中一小股日本兵退入了缅甸境内。整个败逃的过程都是在有序状态下进行的,没有那种狼狈慌乱的迹象,为了鼓舞士气,那位音乐学院出身的队长还带领大家唱歌,而且,在这只队伍里,还有一位对音乐颇有天赋的士兵水岛,他能用缅甸竖琴弹奏国内外美妙的乐曲。当然在这个朴实、聪明的水岛手中,竖琴的功能还不只这些,还可以用来在探路时发信号。直到他们顺利地进入那个缅甸村落里,这部战争题材的影片都没有透露出任何与战争相近的东西,没有残酷、恐惧和血腥的气息,也没有那种通常意义上的战败者的痛苦与迷茫,而这群日本兵也没有我们通常印象中所谓武士道精神之类的表现,相反,看上去更像一群健康乐观的普通日本农民,怀着生存下去安全回家的希望漫无目的地在缅甸的丛林里艰难行进。当他们在那个村落里跟当地人和谐相处的时候,英军包围了上来,这一次,音乐的作用令人难以置信地达到了极致--在那首熟悉的英国民谣歌声里,敌对双方没有交火,而是先后唱和起来,最后人们放下了武器……原来战争在三天前就已经结束了,在这里,投降者没有什么沮丧和痛苦,胜利者也没有什么欢呼雀跃,大家平和地走到了一起,分享战争结束之后的那份难得的宁静和松弛。看到这里的时候,尽管那些朴素而有趣的场景非常有效地保持了观者继续看下去的欲望,但仍会让人不由得产生疑虑,它究竟要讲的是什么呢?就这么下去了?而也就是这个时候,转折开始了:英军包围了另外一小股日军,水岛受命去劝降,但在英军长官所给的三十分钟里,他尽了一切努力也没能达到目的,英军发起了攻击,这股秉承了武士道精神的日军全体阵亡,没能及时离开的水岛也受了重伤。所幸一个僧人救了他的命。恢复过来之后,水岛偷了僧人的衣服,剃掉了自己的头发,冒充僧人往木东方向走去,要到那里的战俘营跟自己的战友汇合。这一路上,他就像个苦行僧一样赤足行进,受了很多的苦,同时也因为这个僧人的身份,受到了普通民众的无私帮助和摩拜,但是真正震动他的并不是这些,而是途中遇到的那些曝尸荒野的日本军人。就这样,他几经周折地到达了木东,看到了战俘营中的战友们,但在偶然看到英军医院的神父跟医护人员为死去的日本士兵唱着安魂曲下葬的场景之后,他改变了主意,决定去把一路上看到的那些日军尸体都安葬好,让他们安息。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大河滩上安葬死者的那个场景,在挖坑的过程中水岛挖到了一颗罕见的缅甸红宝石,受他的感召而来帮助他埋葬死者的一个缅甸人说这颗红宝石可能就是死者的灵魂吧。然后他就带着这颗有着灵魂意味的缅甸红宝石重新去木东,并把它放在骨灰盒里,以日本传统的方式包裹上白布,在一次英军牺牲士兵的安葬仪式上悄然把它存在骨灰存放处。一直不知道他生死的战友们始终都在盼望他回来,然后一起回到祖国,在废墟上重建家园。最后他们马上要被遣送回国的时候,水岛带着那只会说“水岛,跟我们一起回国吧”的鹦鹉,在战俘营外用缅甸竖琴弹奏了一曲,与战友们作最后的道别,然后自己又一次踏上了那条安顿死者灵魂的道路……。这部黑白电影是日本导演市川昆的作品。以前对这位了不起的导演一无所知。他跟黑泽明基本上算是同时代的人,有资料称他与黑泽明、木下惠介、小林正树并称“日本影坛四骑士”。今年的2月13日市川昆以九十二岁的高龄在东京去逝,生前留下的电影作品多达七十五部。这部《缅甸竖琴》是他的成名作,获得了威尼斯电影节的一个特别奖。表面上看这部电影的主题似乎是音乐,在这个并不复杂的故事里,音乐的力量甚至可以改变人的命运,同时也在结构上发挥着至关重要的支撑作用。但细一考量,就会发现,在音乐的线索两边,却是生与死的主题。所以这部影片从一开始就把战争本身的诸多特征都省略了,或者说隐蔽了,在一个更为广阔的层面上来审视具有毁灭力量的战争中的人,一方面是经历了战争幸存下来的那些普通士兵对返乡重新开始生活的渴望,一方面是水岛决定留下来去安顿那些战死者的灵魂的执著信念。面向新生的强烈渴望与安顿死者的执著构成了表面上方向相反,实质上又是注定会在心灵层面完全融合的力量。普通人在战争中变成了野兽、机器,战争结束了,他们需要重新恢复为能够开启新生活的普通人。因而这部影片始终都在透露着那种质朴的普通人所特有的日常乐观精神,他们在失败中并没有精神崩溃,而是努力活下来,努力回到日常状态里,期待着回国重建家园。战争可以把一切变成废墟,但唯一不能毁灭的,或许就是人的灵魂,而需要安顿的,也就是向死而生的人的灵魂,尤其是死者的灵魂。只有把死者的灵魂安顿好了之后,废墟之上才有可能重新生发出一个新的世界,让活下来的人们安心去开启新的生活。留下来以僧人的身份继续去安顿死者灵魂的水岛,尽管在思想上可能还没有达到那种大彻大悟的地步,但在精神上其实还是真的符合僧人的角色,那就是一个佛教意义上的亡灵超度者。这与缅甸这个佛国背景,以及跟日本的佛教传统,确实是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最初作为士兵的水岛或许并不是个佛教徒,但最后他开始这项安顿死者灵魂的事业之时,却又比一般意义上的佛教徒显得更为纯粹和虔诚,通过这样一个过程,他以近乎自我牺牲的方式开始了对自己、对环境、对时代和命运的超越,在那个已然临近大慈悲境界的心怀里,已没有什么是不可以包容的了。然而即便如此,他仍旧是一个世俗意义上的至情者,这一点从他留给战友们的那封信的内容就可以知道。正是这种极深的对人的情感,以及相应的责任感,使得他拥有了非同寻常的悲悯情怀和坚定的信念,而他的信念与行为本身,也就具有了感人至深的、启悟性的博大力量。生存与死亡,在他这里实现了融合,而他就像一个明亮的点,在生死交融处发出光来。市川昆的镜头语言非常的朴素自然,而且在剪辑方面简练平和、毫不拖沓。尤其是在那些大的场景表现方面,特别能看出其眼光的独特,比如开篇部分的那个从空中俯视山野的场面,只是辅以战争的音效,而并没有具体的战争场景,这就既有某种象征意味--使得大地山野如同一张巨大的有些扭曲模糊的面孔,又让人觉得这确实是自然本身的一个景观现实,并没有介入明显的人为增加上去修饰的东西,战争的事实确实使得这个巨大的背景发了生很多变化,但又并不会持续保存下来,这个背景似乎转眼间就能恢复原来的样子,并在这个恢复的过程中淹没了此间发生的那些诸多事件的痕迹,给人以空荡而又混沌的原初感觉,一切又都回到了零起点上。再比如水岛在山上发现山谷里有很多日军腐败的尸体正被鹰群反复侵食的场景,那种远景视角下微小的尸体像肢解的玩偶似的堆陈在那里,与高空中纷纷飞旋的老鹰构成了悲凉的对应,死亡的现场理应是惨不忍睹的,但这里市川昆并没有强调这一点,而是更多地强调了已然变成物质的人体是如此的微不足道但又令人怜悯的那一面,在此刻人的尸体跟其它物种的尸体固然是全无差别的,但是这里面又确实蕴含着巨大的不安与沉痛,在人的眼中,即便是已然变为物质的人也还是需要有所安顿的,否则的话死去的人的灵魂就可能受到拖累而找不到托寄之处。还有就是水岛在大河边安葬死者的场面,那条平静灰亮的河流仿佛就是生与死的边界,他在这里倾尽全力去安葬死去的人们,为的就是让彼岸的仍旧活着的人们能够安心,同时也让此岸的所有死者得以安魂,而更进一步讲,无论生者还是死者,都是时间之流中的不同的组成部分,灵魂安顿好了之后,这条漫无尽头的时间之流才能更为博大深厚地流向远方……在这个场面里市川昆所采取的多是广角视界,整个画面始终都在那种溟茫寂寥悠远的气氛里呈现,而当那颗缅甸红宝石的特定镜头出现的时候,尽管它并没有什么夺目的异彩,却让此前的那些深沉浑茫的画面所隐含的力量都汇聚到这个亮点上,爆发出瞬间就能刻骨铭心的效果。此外还有一些小场景也拍得很精彩,像在那个小村落里一群日本兵为了麻痹英军而载歌载舞把那车弹药弄到安全地带的场景,特别容易让人联想到日本民间节日里的某些祭祀欢庆的场面,而后来在缅甸的寺庙间英军举行安葬牺牲者的仪式上,那种仿佛仙境般的镜头与音效的结合处理也很见功夫。通过各种各样的场景的流动与变化,你会发现,其实在市川昆的眼中,到头来人就是普通意义上的人,既便是经历了战争的洗礼,也并没有显得更高大或更渺小,在天地之间,他们显得如此脆弱,同时也有其特有的坚强,他们的生命是如此的短促,同时他们对生死的参悟以及对灵魂的关注,又使得他们的生命过程哪怕是非常短促的似乎也还是有着很多新生的可能。
你怎么评价《缅甸的竖琴》这部电影?
信中也有两句,比如“我们为什么要遭受这样的痛苦,世界为什么会这样。。。我们所能做的就是抚平战争的创伤。。。” 这句话,到了这儿,与其说是反省,不如说是装饰。如同影片中的寺庙,佛像,僧人,都成了影片的装饰,他们的作用是为日本军人哀悼,他们的慈眼看到的是散落在缅甸土地上的日本军人的遗骸。M不愿意回去,是因为他要把所有日军的尸体掩埋。他把那颗从河边挖出的宝石放在骨灰盒里,是代替所有日军的亡灵放进盒里,而且埋在睡佛里;而并不是埋葬那个曾经的军人,那个所谓的我认为已经死去的他,那个为日本战斗的战士。他仍然是个军人,日本军人,只是他的军礼变成了双手合十。他不配作僧人。从头至尾,我都在自作多情,以为他在反思,影片在反思。而自作多情来自于我的立场,因而竟然忽视或者误读了电影的语言和意象。如果影片真的在我认为最应该结束的时候,就以M告别战友的沉沉暮色画上句号,自作多情就成功了。幸好,不是。于是,最后那一笔给影片重重地盖上了封印:一部关于二战的日本的自我怜惜的影片,虽然反对战争,却看不到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起者对于战争的一点点反思和自省,对于其他国家的人民造成的创伤的愧疚。在影片中受到了怜悯的只是失去了生命的,或者残缺身体的日本军人。而反对战争的几个片断,竟然最终沦为了装饰。影片里,日军和英军在丛林的月色中唱着“我的甜蜜的家”走到一起的美好,因之黯然失色。影片伊始,银幕上的字幕是“缅甸的土地是红的,岩石也是红的。”影片结束的时候,镜头里仍旧回到缅甸的土地,出现相同的字幕“缅甸的土地是红的,岩石也是红的。”好想说一声:老大,那土地和岩石不仅仅有你们日本军人的鲜血好吧?何况,难道有谁请你们来染红?
孔雀东南飞里“箜篌”是什么乐器
箜篌(kōnghóu)历史悠久、源远流长,音域宽广、音色柔美清澈,表现力强。古代除宫廷雅乐使用外,在民间也广泛流传。现常用于独奏、重奏和为歌舞伴奏,并在大型民族管弦乐队中应用。箜篌在古代有卧箜篌、竖箜篌、凤首箜篌三种形制。竖箜篌东汉之时,由波斯(今伊朗)传入我国一种角形竖琴,也称箜篌。凤首箜篌凤首箜篌在东晋时自印度经中亚,传入我国,明代后失传。卧箜篌卧箜篌与琴瑟相似,但有品,是汉民族的传统乐器,盛行于汉至隋唐,宋代后失传。在朝鲜却得以传承,经过历代的流传和改进成为今日的玄琴。小箜篌我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弹拨弦鸣乐器。又称角形箜篌,是竖箜篌之一种。现代有改进款现代箜篌,不一一列举了。
孔雀东南飞里面的箜篌是一种什么乐器
箜篌( kōnghóu) 是十分古老的弹弦乐器,最初称“坎侯”或“空侯”,文献中有“卧箜篌、竖箜篌、凤首箜篌”三种形制。 箜篌历史悠久、源远流长,音域宽广、音色柔美清澈,表现力强。古代除宫廷雅乐使用外,在民间也广泛流传。现常用于独奏、重奏和为歌舞伴奏,并在大型民族管弦乐队中应用。箜篌在古代有卧箜篌、竖箜篌、凤首箜篌三种形制《史记·封神书》:“于是塞南越,祷祠太一,后土,始用乐舞,益召歌儿,作二十五弦及空侯琴瑟自此起。”唐代杜佑《通典》:“汉武帝使乐人侯调所作……今按其形,似瑟而小,七弦,用拨弹之如琵琶也。”此属琴瑟类的卧箜篌。从甘肃省嘉峪关魏晋墓砖书看,其面板上没有品柱。竖箜篌,汉代自西域传入,后被称为“胡箜篌”。《隋书音乐志》记载:“今曲项琵琶、竖头箜篌之徒,并出自西域,非华夏之乐器。” 从古代大量演奏图像中所绘的竖箜篌和日本奈良正庵院保存的我国唐代漆箜篌和螺箜篌残件看,它的音箱设在向上弯曲的曲木上。凤首箜篌形制似与竖箜篌相近,又常以凤首为装饰而得名,其音箱设在下方横木的部位,向上的曲木则设有轸或起轸的作用,用以紧弦。正如《乐唐书》所载:“凤首箜篌,有项如轸”,杜佑《通典》:“凤首箜篌,头有轸”。有轸或无轸的图像在敦煌壁书中均有所见。凤首箜篌自印度传入,用于隋唐燕乐中的天竺乐,至宋代隋炀《乐书》中仍绘有当时存在的多种形制的箜篌,明代以后失传。 据考证,箜篌流传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箜篌在古代除宫廷乐队使用外,在民间也广泛流传。在中国盛唐(618-907)时期,随着经济文化的飞速发展,箜篌演奏艺术也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也就是在这个时期,中国古代的箜篌先后传入日本、朝鲜等邻国。在日本东良大寺的寺院中,至今还保存着两架唐代箜篌残品。但是,这件古老的乐器,从十四世纪后期便不再流行,以致慢慢消失了,人们只能在以前的壁画和浮雕上看到一些箜篌的图样。